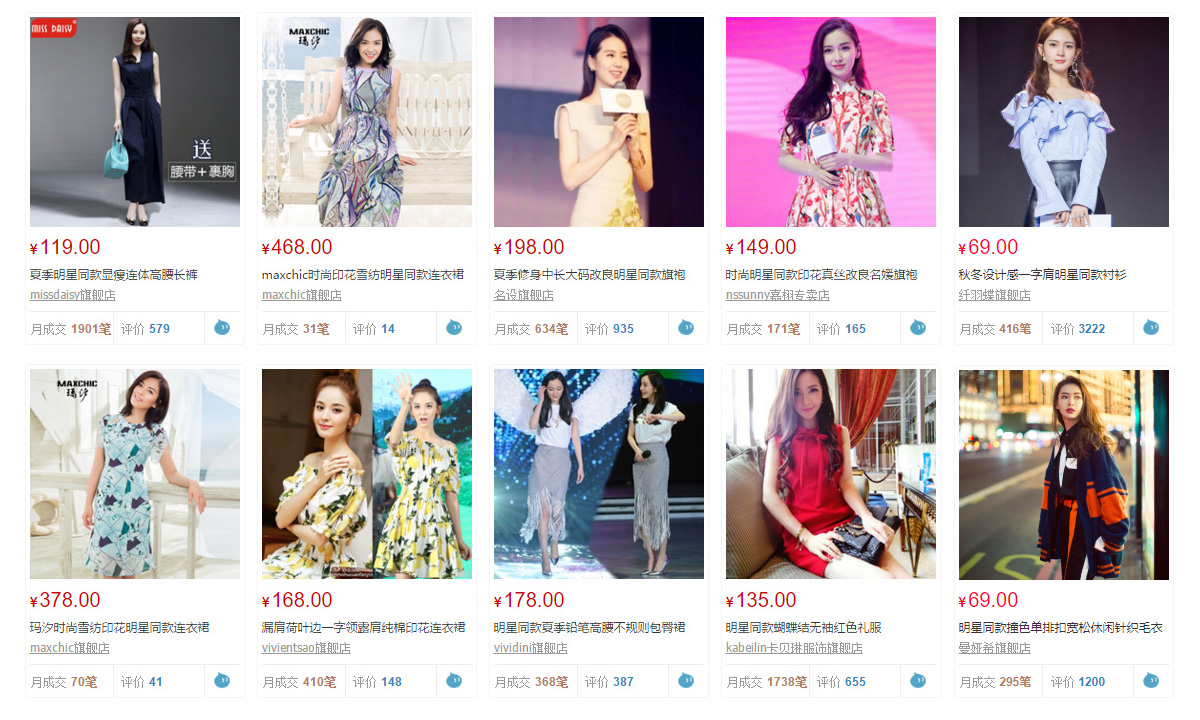| ���� | ���� |
|---|---|
| ���� | �й� |
| ��Ҫ�ɾ� | 83�桶��¥�Ρ��������� |
����Ҳ����һ��������־�����ˣ����Ҳ�ϲ������Ȧ��ȷ��˵���Ҳ�����Ӧ���ָ��ӵ������Ȼ20��ǰ�ڵ�Ȧ�ӱ����ڴ����ö࣬��һЩ���������Ѿ���ʼ̧ͷ���� ����
10������й�Ϸ��ѧԺ�����������������ڵ���Ϸ����������Ϊ���ǿư�ġ�����ֻ��������������С����Ϸ����IJ�����ưࡣ��ƾ�ŵ�ʦ�ž�����ʦ�ľټ����������롶��¥�Ρ����飬�ʹ�������������������֪�������ұ����Ը�������кܴ�ͬ������������̣������˲���������������������
1986�꣬����¥�Ρ�����������ź������̬����5ԪǮ�����μ��˱�����һ�����ִ���������һ��ھ��Ǻ춹��������������û�����������Ǵα����ϣ��������˺��Լ����18��İ�����Խ�����������д�ˡ�ѪȾ�ķ�ɡ����á��������¡������й�����������ӡ���һ��д���ҵڶ����ݳ���ַ��ֽ������ʰ��������������ͨ��40���ӵĵ绰������Խ����һ�����顣
��������һ�����°ɡ����������䡣���϶�����������Խ���������������������ʶ��һ�����ڣ���Լ��ȥ���Ĺ������棬���������������Խ˵������ʵ����Ԥı�������ǽ���ֱ�������ί����Ԥ����ʼ�Ҿ��������ˡ������ҵĹ����ҳ����������ϣ���ҵĸ����ܴ������ҳɹ��ˡ��� ����
������ʼ����ɬ������֪��������д��ѪȾ�ķ�ɡ������Ժ��Һܳ�������������������ġ��������¡��������������IJŻ�����ʱ����������裬˵��̳���Ѿ��С�һ�����С��ˣ���������֣�û�ҵĹ�����������ܾ���Զ�������˳������ˡ��� ����
һ����ת�۹�ȥ������������ʽ����������˵�������ܱ��أ����ڴ���ϣ�����������Ҫǣ�����֣������ϣ�˵�±��˼ҿ������ߡ�˵ʵ�ڵģ����Ⱳ��Ҫ��û�����ҿ���ô�������϶����úܷ�ζ������ԽҲ��ʾ���������Ƕ�����˵����һ�����ã�һ������������أ��������ö�һ�㡣�����뷨�����пգ�������������Ӧ�����������������ҵ�С���ࡣ��
1988�꣬��Խȥ�ձ��������֡�����ȥ�ձ�������ÿ�¹�绰�Ѿ�12����Ԫ�����ң��������������ְ��ĵ�˼�����Խ�ߺ������£����������Сβ�͡�Զ�ɶ�孡� ����
����˵������ʼ���ǹ��úܿࡣ����Խ˵������ʱ������Զû������Ǯ����ѪȾ�ķ�ɡ�����ֻ����36ԪǮ�����������¡���Щ������76Ԫ���������ǵ�����Ԫ����������Խ��������һ��ơ�ƣ�һ��Ӳ�ò����˵����������ڹ㳡�ϣ�һ��һ��ơ�ơ�һ���������������ֵ���Ⱥ����Ȼ��࣬����Ȼ���ġ��� ����
������һ��������Թأ���Խ�͵�����ϴ���ӡ�������ʲô���ɡ����д�ȥ��Խ�ĵط�������������ձ��˾�Ȼ���ۣ���Ů������ô������ô�����ˣ���ʱ�Ҷ����Ǻ���˵���������й����вŻ��������ˡ������������ձ��������������ɰ�����ȥ�������������Щ��ѧ������ʶ�������Ű����ɻ�ر��������Ϻ��ˣ�ÿ�λ����������Եģ������˸ж�����ϧ���ڲ��ǵ����������ˡ���1989��4�£������Կ����о�Ա�����ݣ������ձ��絾���ѧ�о�����Ϸ��Ƚϣ��������룬����ԽҲ�ͷɵ���Ƭ��˾ǩԼд�裬�����ս���ת��
1991��2��25�գ��������ձ����˽��֤��֮����Խѧ�ɹ������ʱ���������ձ�Ϸ���С���������������Ⱳ�Ӻ����Ű������ߡ�����Խ�ߺ�һ���ڣ�������绰����˵������������������㡣����Խ˵��������Ͻ�ȥ���Ʊ������ʱ�������в���һ������õ���ʿѧλ������ѡ���˻ع���1991��5��26�գ������ڹ�����ʽ��顣 ����
�ص����ڣ���������Խһ���������Ļ���ҵ����ʵ��1990���ʼ����Խ�Ϳ�ʼ��̨�������ڵص������װ����������Ҳ���ڵظ�̳���ͼ���װ�ĵ�һ�⡣�����ձ����ܽ磨����Ȧ�������൱�˽�İ�������ʱҲ�ͳ��������������֡����й���һ�����������������������ҵİ�����֪������ô�������ˡ���1992�꣬������Խ�����ڷ��ֵĻƸ�ѡ���ر������������������ڼ������Ż�Ͳһ���̳����ġ���
10������й�Ϸ��ѧԺ�����������������ڵ���Ϸ����������Ϊ���ǿư�ġ�����ֻ��������������С����Ϸ����IJ�����ưࡣ��ƾ�ŵ�ʦ�ž�����ʦ�ľټ����������롶��¥�Ρ����飬�ʹ�������������������֪�������ұ����Ը�������кܴ�ͬ������������̣������˲���������������������
1986�꣬����¥�Ρ�����������ź������̬����5ԪǮ�����μ��˱�����һ�����ִ���������һ��ھ��Ǻ춹��������������û�����������Ǵα����ϣ��������˺��Լ����18��İ�����Խ�����������д�ˡ�ѪȾ�ķ�ɡ����á��������¡������й�����������ӡ���һ��д���ҵڶ����ݳ���ַ��ֽ������ʰ��������������ͨ��40���ӵĵ绰������Խ����һ�����顣
��������һ�����°ɡ����������䡣���϶�����������Խ���������������������ʶ��һ�����ڣ���Լ��ȥ���Ĺ������棬���������������Խ˵������ʵ����Ԥı�������ǽ���ֱ�������ί����Ԥ����ʼ�Ҿ��������ˡ������ҵĹ����ҳ����������ϣ���ҵĸ����ܴ������ҳɹ��ˡ��� ����
������ʼ����ɬ������֪��������д��ѪȾ�ķ�ɡ������Ժ��Һܳ�������������������ġ��������¡��������������IJŻ�����ʱ����������裬˵��̳���Ѿ��С�һ�����С��ˣ���������֣�û�ҵĹ�����������ܾ���Զ�������˳������ˡ��� ����
һ����ת�۹�ȥ������������ʽ����������˵�������ܱ��أ����ڴ���ϣ�����������Ҫǣ�����֣������ϣ�˵�±��˼ҿ������ߡ�˵ʵ�ڵģ����Ⱳ��Ҫ��û�����ҿ���ô�������϶����úܷ�ζ������ԽҲ��ʾ���������Ƕ�����˵����һ�����ã�һ������������أ��������ö�һ�㡣�����뷨�����пգ�������������Ӧ�����������������ҵ�С���ࡣ��
1988�꣬��Խȥ�ձ��������֡�����ȥ�ձ�������ÿ�¹�绰�Ѿ�12����Ԫ�����ң��������������ְ��ĵ�˼�����Խ�ߺ������£����������Сβ�͡�Զ�ɶ�孡� ����
����˵������ʼ���ǹ��úܿࡣ����Խ˵������ʱ������Զû������Ǯ����ѪȾ�ķ�ɡ�����ֻ����36ԪǮ�����������¡���Щ������76Ԫ���������ǵ�����Ԫ����������Խ��������һ��ơ�ƣ�һ��Ӳ�ò����˵����������ڹ㳡�ϣ�һ��һ��ơ�ơ�һ���������������ֵ���Ⱥ����Ȼ��࣬����Ȼ���ġ��� ����
������һ��������Թأ���Խ�͵�����ϴ���ӡ�������ʲô���ɡ����д�ȥ��Խ�ĵط�������������ձ��˾�Ȼ���ۣ���Ů������ô������ô�����ˣ���ʱ�Ҷ����Ǻ���˵���������й����вŻ��������ˡ������������ձ��������������ɰ�����ȥ�������������Щ��ѧ������ʶ�������Ű����ɻ�ر��������Ϻ��ˣ�ÿ�λ����������Եģ������˸ж�����ϧ���ڲ��ǵ����������ˡ���1989��4�£������Կ����о�Ա�����ݣ������ձ��絾���ѧ�о�����Ϸ��Ƚϣ��������룬����ԽҲ�ͷɵ���Ƭ��˾ǩԼд�裬�����ս���ת��
1991��2��25�գ��������ձ����˽��֤��֮����Խѧ�ɹ������ʱ���������ձ�Ϸ���С���������������Ⱳ�Ӻ����Ű������ߡ�����Խ�ߺ�һ���ڣ�������绰����˵������������������㡣����Խ˵��������Ͻ�ȥ���Ʊ������ʱ�������в���һ������õ���ʿѧλ������ѡ���˻ع���1991��5��26�գ������ڹ�����ʽ��顣 ����
�ص����ڣ���������Խһ���������Ļ���ҵ����ʵ��1990���ʼ����Խ�Ϳ�ʼ��̨�������ڵص������װ����������Ҳ���ڵظ�̳���ͼ���װ�ĵ�һ�⡣�����ձ����ܽ磨����Ȧ�������൱�˽�İ�������ʱҲ�ͳ��������������֡����й���һ�����������������������ҵİ�����֪������ô�������ˡ���1992�꣬������Խ�����ڷ��ֵĻƸ�ѡ���ر������������������ڼ������Ż�Ͳһ���̳����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