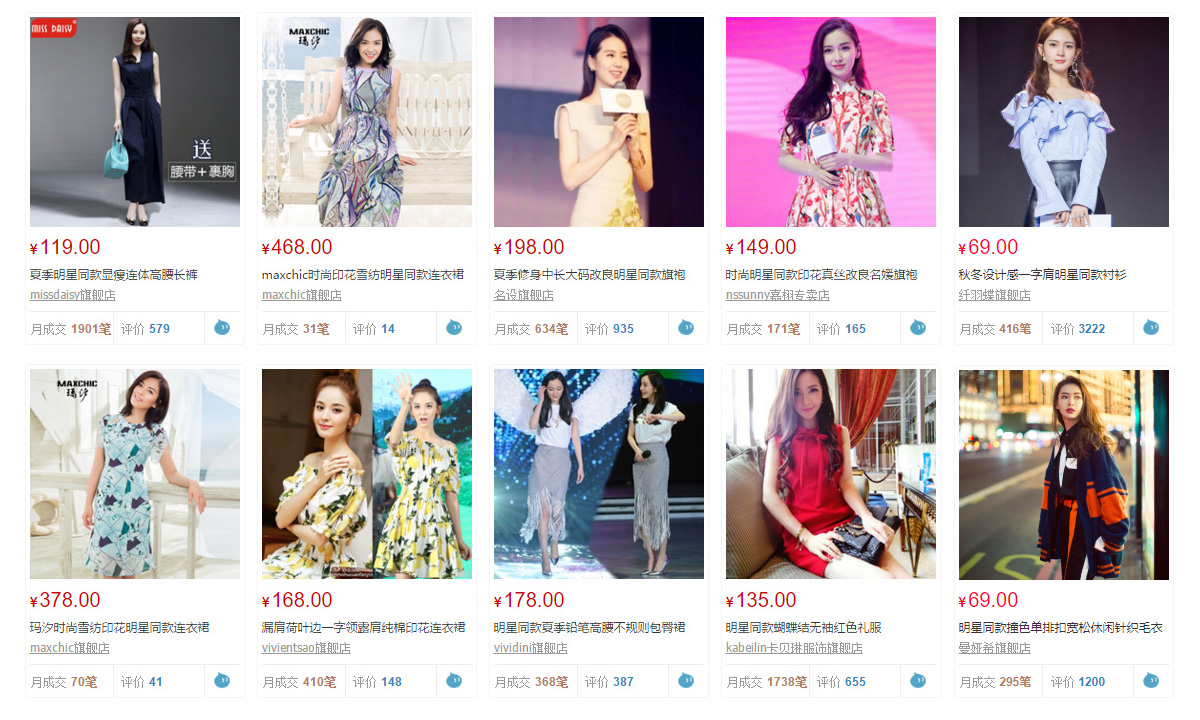| 姓名 | 许广平 |
|---|---|
| 笔名 | 景宋 |
| 国籍 | 中国 |
| 民族 | 汉 |
| 出生地 | 广东番禺 |
| 出生日期 | 1898年2月12日 |
| 逝世日期 | 1968年3月3日 |
| 代表作品 | 《两地书》 |
| 丈夫 | 鲁迅 |
| 儿子 | 周海婴 |
许广平:广州“奇女”首席代表
无论是幼时的拒绝裹脚、争取到与兄弟们一起进私塾念书的机会,还是强烈要求解除婚约,冲破包办婚姻的牢笼,都已经让许广平不为世俗观念所囿的个性凸显出来。而考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在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当中,许广平已经在为自己的人生道路找到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并且一直走了下去。进入到“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许广平仍然本性不改,她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带领同学发起了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不羁的性格甚至让她被杨荫榆冠以“害群”的称号。
然而,正是她的不“安分”,正是性格中的淘气和放肆,让许广平遇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导师、战友、伴侣——鲁迅先生。
从师生友谊到后来那场惊动天下的爱情,许广平并非不知道,那个年代的社会舆论,是容不下她与鲁迅的这种爱情的。面对坚如壁垒的传统意识,面对流言横飞的中伤,她决心以自己的主动出击来争取个人幸福。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的笔名发表《同行者》,大胆表示不慑于“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卫道士的“猛烈袭击”,“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而在《风子是我的爱》中,她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强烈的爱情宣言背后,是隐藏在许广平性格命运中的一贯底色。
在爱情受到重重阻隔的日子里,许广平从来没有考虑过退缩。与鲁迅同车南下,鲁迅带着犹豫、彷徨的心态去了厦门,许广平以极为主动的方式让鲁迅打消了种种顾虑,不到半年之后,便下定决心离厦门到广州,与许广平真正走到了一起。在这段备受磨难的爱情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广州女子身上所蕴藏的巨大力量。
与鲁迅居住在上海的十年间,许广平展示出来的,是与之前积极主动的现代女性形象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侧面。我们今天已经很难体会.从一个叱咤风云的妇女运动领袖到一名家庭妇女,需要何等的牺牲精神与勇气。但许广平毕竟是许广平,即使牺牲的意向已定,仍然要保留她自己的某种独立性。蒋锡金先生所写《长怀许广平先生》中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许广平始终把鲁迅收入和她自己曾经有的一笔收入严格地分开,这是她在广州教书时积蓄下来的三百元大洋,放在她自己的存折上。她是反对妇女婚后成为男子的附属品的,她说,当然,她不会和周先生分开,但也要设想,万一发生不得不离开的情况,她可以不依赖别人的资助,用这三百元维持自己几个月甚至半年的生活。
了解鲁迅生活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他的夫人决不是他卧室里的一件安适的家具,她乃是他的共同工作者。在某些地方还是他的右手。离开她,他的生活便不可想像。”
广州奇女子许广平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她所具有的人格力量,更有贯穿其一生的执着。后人在面临追求理想与幸福过程中的困惑时,是否仍可以感受到一种力量的存在?
世家叛逆
许氏家族1772年迁居到高第街,从经商到入仕再到后来的官宦世家,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知名人物。
许广平因为一出生便尿遗母腹,哭声洪亮,被认为是“克父母”。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碰杯为婚”,将许广平许给了一个姓马的劣绅家。辛亥革命后,大哥经常向她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许广平深受影响,不仅坚持不裹脚,还争取到了与兄弟们一起到私塾读书的机会,更坚决反对父亲给自己包办的婚姻。1917年父亲病逝后不久,她开始用生活独立来争取婚姻自由,与二哥商量与马家解除婚约,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出一笔钱让马家娶一个小妾替代。包办婚姻终于没有成为束缚许广平的牢笼。
学潮害马
在天津女师期间,许广平已经接受了进步思潮,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了“五四”运动。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是骨干和领导者,发动了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学潮运动,结果杨以闹事为名开除六名学生,以免“害群”。“害群”即害群之马,鲁迅后来送给许广平以“害马”之称。
学潮期间,她最重要的收获是结识了导师鲁迅。刚开始时,她与同学们一样非常仰慕鲁迅先生。不过,总是坐在第一排、好提问题的她,逐渐感觉到鲁迅先生并不“怪僻可怕”后,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而鲁迅也认为她有才气,颇有好感。在他的指引下,许广平开始在思想文化战线崭露头角,发表了大量文章。
广州爱情
鲁迅与许广平的恋情真正公开是在广州。1926年,鲁迅南下厦门,许广平回广州,两人约好用两年的时间,解决经济上的问题。但半年之后,鲁迅便应中山大学之聘也到了广州,这与他不满厦门的气氛有关,但更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被爱情吸引。据说在厦门时,陷入热恋的鲁迅晚上写完给许广平的情书后,常常等不及第二天早上,常常在深夜越过铁栅栏去寄信。
到达广州后,鲁迅和许广平的恋情基本公开,不仅接连外出游览、看电影,有来客来访时许广平也不再回避。刚开始时鲁迅与好友许寿裳同住大钟楼,后共租白云楼二楼,许广平也搬过去同住。这可以看做是两人爱情的正式宣言。
鲁迅与许广平在广州正式开始的爱情,对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两人共同生活的1O年里,鲁迅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数量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鲁迅还特意写过一篇《如此广州》,他认为广州人迷信风气过盛,却蕴涵着一种很认真的精神,这点非常可贵,因为当时中国人的国民性里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马虎”。
流言伴侣
因为鲁迅形式婚姻的存在,因为两人的师生之名,从一开始起,他与许广平的爱情就注定要面临流言的中伤。
鲁迅到厦门不久,北京和上海便已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大有双宿双飞之态”,而此时他们并没有同居。1928年,鲁迅和许广平正式同居不到半年,收到一封自称是鲁迅崇拜者的信:“昨与×××诸人同席,两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
尽管面临着沉重的社会压力,尽管也有过犹豫,但鲁迅和许广平最终没有选择退缩。鲁迅鼓励许广平到中山大学给他当助教:“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对语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鲁迅和许广平去杭州游玩时,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个孩子。许广平用自己炽热的爱和她性格中特有的开朗直率,让在有名无实的婚姻中自我幽闭二十年的鲁迅焕发出生命活力。
许广平后来解释说:“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鲁迅也承认,在他们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比他决断得多。
许广平相关资讯
-
鲁迅与许广平的惊世忘年恋
2015-07-10 / 27942 Views / 0 Comments”当然无可置疑的,这十年是凝聚着许广平诚挚的感情与辛勤的劳动,“十年携手共艰危”,他们艰危与共、相濡以沫,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表达的是人间的至爱
-
《旗袍与名媛》--许广平旗袍上的纽扣洗脱了
2015-07-10 / 7869 Views / 0 Comments萧红与许广平在花园里照相。由于洗的次数太多,许广平旗袍上的纽扣都掉了,只好让萧红站在她面前遮挡,省下的钱都印了书和画
-
鲁迅一生数段情缘:红颜知己多才女
2013-02-10 / 7800 Views / 0 Comments说到鲁迅,毋庸置疑,鲁迅确实是民国时代的革命斗士,文学泰斗。其文风劲道,其风骨超然。但鲁迅虽是斗士,却非鲁圣。我们要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人,他第一个标准是人,不是神!谈起鲁迅的女人,不少人被教材所误,只知道有其学生兼夫人许广平,然后一些人知道鲁迅还有个原配
-
揭秘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4对师生恋
2012-03-22 / 38092 Views / 0 Comments由于古代中国的学堂基本不招女生,女人很少有上学的机会,所以中国的师生恋始于晚清和在民国开始流行。西风东渐,私塾多变为学堂,女孩子走出绣楼和闺门,也开始进学堂接受现代教育。这得以让她们接触到许多风流倜傥才学渊博的老师。
-
民国爱情“十大最”哪对是天作之合?
2011-10-22 / 7866 Views / 0 Comments最是难以评说的爱情:徐志摩与陆小曼。有才情的人容易感情冲动,陆害怕这个感情丰富的才子移情别恋,对其看护甚严,不许徐再有取妾的打算。徐对陆用情专一,可是徐死后,陆却与翁瑞午同居,陆小曼依然相信爱情?还是我们没有参透爱情的真谛?而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实在找
-
鲁迅名言中的经典幽默
2011-10-20 / 27069 Views / 0 Comments鲁迅先生一生中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融讽刺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尤其是他的打油诗辛辣有加,妙趣横生,且人木三分。如鲁迅先生曾写的《南京民谣》打油诗:“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揭露国民党的内部摩擦,对他们伪装正经的行为进行辛辣的讽刺
-
鲁迅只因原配妻子不漂亮而不接受她吗?
2011-09-15 / 26545 Views / 3 Comments在鲁迅的生活中,有一个人是绝对绕不开的,尽管他们名为夫妻,却名存实亡,形同路人,这个人就是鲁迅的夫人朱安。三十多年前,开始接触鲁迅作品的时候,我只知道他的爱人是许广平,而朱安的名字却始终被回避被隐藏,她和鲁迅的夫妻关系显得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生前死
-
马珏与鲁迅 爱藏于书中
2011-06-02 / 1827 Views / 0 Comments马珏十分尊敬鲁迅,与许广平不同。如果她对他产生热烈的感情,如许广平那样爱慕他,会不会又出来一段情史呢?
-
鲁迅与许广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
2011-05-16 / 5726 Views / 0 Comments1925年3月11日清晨,随着一阵晨铃响起,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宿舍内,学生们纷纷起床梳洗,准备这一天即将开始的课程。而此时,这栋小楼二层的一间宿舍里,一位女学生正在给自己的老师写一封信,信中说: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留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饼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