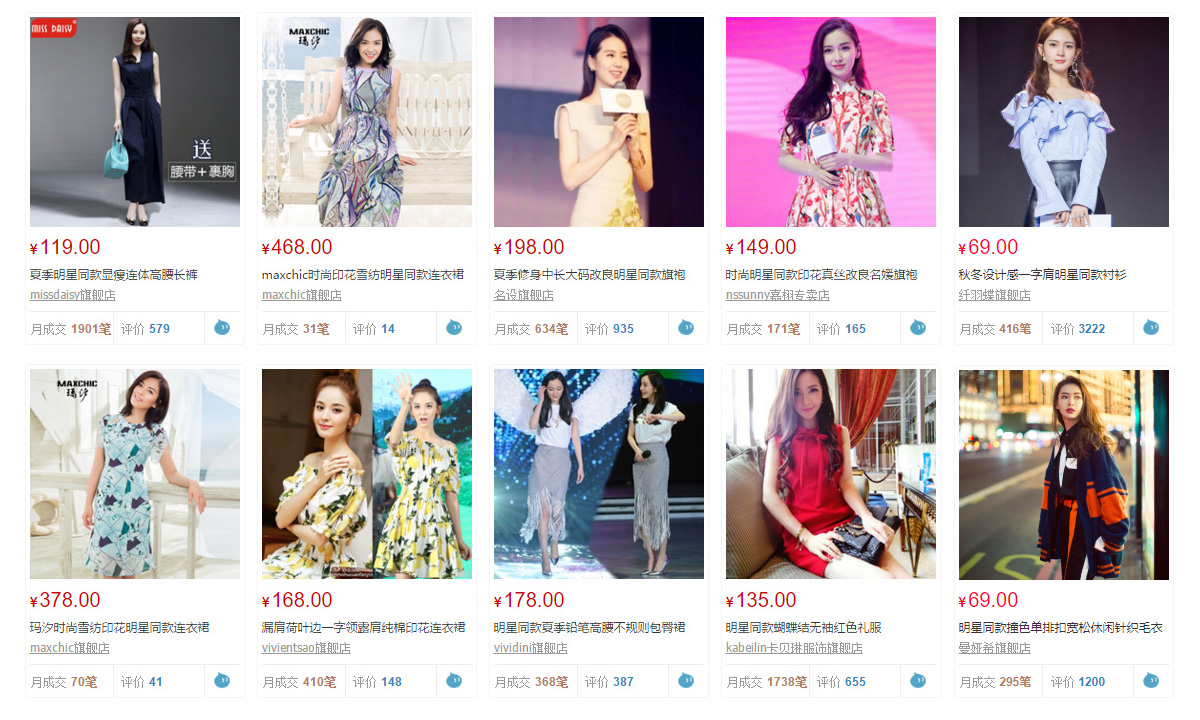| 姓名 | 杨步伟 |
|---|---|
| 国籍 | 中国 |
| 出生地 | 南京 |
| 出生日期 | 1889 |
| 逝世日期 | 1981 |
| 职业 | 校长 |
| 毕业院校 | 东京帝国大学 |
| 主要成就 | 合办一所私立医院“森仁医院” |
| 代表作品 | 《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华食谱》等 |
杨步伟出生于南京望族,是一个具有非凡资质的女子。1912年(22岁),她便担任了中国第一所“崇实女子中学”的校长。后来,到日本学医,191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绒线胡同和一位同学合办一所“森仁医院”。
杨步伟与赵元任
尽管关注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已经很长时间了。直到今天,我还说不清楚,是杨步伟让赵元任走向普罗大众还是赵元任让杨步伟名声远播。或许,这只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悖论。他们相敬如宾,珠联璧合的情感生活,本身就是一段历久弥新的佳话。
杨步伟祖籍安徽石台,1889年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按照传统习惯,一岁时要“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后来,杨步伟对此解释道: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或许,苍天在冥冥之中已经无言地把人生的运程展示。这些,在她以后的人生中似乎都得到了应验。
幼年时的杨步伟天真烂漫,无拘无束。因她脚大,家里人喊她叫大脚;因她小时瘦而高,送给她“天灯杆子”的绰号;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干。家里人亲昵地骂她“搅人精”。
优裕的家境,是她从小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先生教她《论语》,当读到“割不正不食”时,她批评孔子浪费:“他只吃方方正正的肉,那谁吃他割下来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父母骂她不敬圣人;读《百家姓》,她取笑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王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一副童言无忌的样子。
1895年,杨步伟的生父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的施工管理。正在两江总督张之洞门下的黎元洪负责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杨步伟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黎元洪和她闹着玩,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说她放的雪人弄湿了他的被子。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还了五下,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黎元洪对杨步伟十分欢喜,杨步伟从日本学医归来后,得到了黎元洪十万元的捐助,她的医院才得以开张。
16岁那年,杨步伟参加南京旅宁学堂考试,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这样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在那个男权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不啻是一声惊雷!然而,和绝大多数女子一样,彼时的她并没有摆脱家庭的羁绊:刚出生前父母做主与表弟指腹为婚。就在这年,家里正式下了定婚礼,要她嫁给二表弟,她不干,坚决要退婚。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要死要活,家里被闹得鸡犬不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了,但要她声明终生不嫁。生父气得半死,要将她捉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开明的祖父出面,才收了场。她以不屈的抗争换回了自由,这场胜利,使她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1912年,时任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办了崇实学校,培养训练500多人的北伐女子敢死队员。22岁的杨步伟担纲当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结绒绳,刺绣,学救护,轰轰烈烈。还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赵元任与杨步伟的恋爱始于1920年。那是9月的一个晚上,赵元任从国语统一会散会出来,因时间太晚西直门城门已关,回不了清华,就去表哥庞敦敏家过夜。那天表哥家正好有客人,都是留学日本归来的朋友,其中两位是森仁产科医院的女医生杨步伟和李贯中,第二天两位女医生请庞敦敏夫妇到中央公园吃饭,作为庞家客人赵元任也应邀请做客。赵元任对两位女医生印象很深刻,称她们“这两位大夫是百分之百的开通”。
饭后大家到杨步伟的森仁医院,他们吃了法国点心,美国巧克力糖,赵元任唱美国歌,表哥表嫂唱昆曲。从此赵元任便成了森仁医院的常客,杨步伟在自传里说,她本想成全赵元任和李贯中的结合,自己尽量躲开,谁知最后成全的却是赵元任和杨步伟。
那时,英国哲学家罗素正在北京讲学,有一次同杨步伟出去游玩回来晚了,罗素只好坐在讲台上干等着,当他看见赵元任带着女朋友进礼堂时就全明白了,罗素指着他笑着轻轻说:"Badboy,badboy!"
赵元任后来记述了他与杨步伟如何确定终身大事的细节:“(1921年春)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韵卿(杨步伟)问明天早上能不能去看她,她说可以,她会在家的。我说我要在中山公园西山坡上见她。七点钟她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山顶上等了。‘你那么高啊!赵先生。'这是她说‘早哇'的另一种方法。我走下山坡对她说:‘杨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可是我怕你可能伤害她,而对她没有好处。我愿意一切美好,不过我不能老让她误会。也许像我以前说的,我应该少来看你们,可是为什么我该--'我说了半句停止不说了,和她在公园里静静地走来走去,最后在公理战胜碑前停下来,她说:‘对了,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于我也最好。'说了她就转身走开。‘韵卿(杨步伟的字)!(这一回才终于叫出了名字)'我亲切地叫她,她回过头来。‘韵卿,'我又叫一声,‘就那么算了吗?--我是说咱们?'我怕她会回答:‘咱们?怎么叫咱们?'但是她未作声,向我走过来。”
1921年6月1日,32岁的杨步伟和29岁的赵元任举办了一场独出心裁的婚礼。这一天上午,他们在北京市小雅宝胡同49号住处,请老朋友胡适还有杨步伟的同行朱徵小姐一块儿吃饭。
由杨步伟亲自下厨做四样美味的小菜。饭后,赵元任微笑着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朱徵大夫和胡适先生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回忆道:“我的同班同学胡适劝我们至少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才算合法。”
然后,赵元任杨步伟到中山公园,自照了多张相片,决定以在格言亭拍的一张,跟“结婚(或无仪式结婚)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写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
在发给亲戚和朋友们的结婚通知书上,他们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们末到之先已经在“十年六月一日(就是西历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通知书上定的结婚的那时刻,两个人正在邮局给亲友发给结婚通知书呢。
翌日,《北京晨报》以“新人物新式婚姻”为标准题,“新夫妇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证婚人胡适之与朱徵女士”“新式婚书”“新式的通知书”四个副标题报道了他们的结婚消息。报上说这个结婚式不但在中国,就在世界,也算得一种最简单最近理的结婚式。当赵元任问罗素这种没有仪式的结婚仪式是否太保守时,罗素回答“这够激进了!”
事后,这对不谙人情世故的书生还因为真的退掉礼物而得罪了亲戚。最喜爱赵元任的姑妈送来一个花篮,也被退回了——因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但此后赵元任一直在追悔,那个花篮总可看作精心制作的祝贺卡片呀!
对于他们不落俗套的婚礼,杨步伟一直引以为豪:“我们当时这无仪式的结婚仪式,不但是在那时轰动一时,就是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要说学赵元任夫妇的结婚仪式,但是没有一次学象了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女儿们也学不象。”
婚后,杨步伟舍弃了自己主持的医院院长和妇科主任职务,当做起了“全职太太”。但她是位“闲着就难受”的女性。
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太太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佯作不知,不闻不问,落得个清净。而杨步伟依旧我行我素,乐此不疲。遗憾的还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反而赔本关张,杨步伟投资的400银圆全砸进去啦。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退出了小饭馆,杨步伟又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还办了个“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以至遭到政府“窝匪罪”的指控,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杨步伟重情仗义,古道热肠。她的的同学林贯虹病死后,她张罗着将她的遗体送回老家福建安葬。她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帮助死者亲属。后来,清华大学为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创办了成志小学,请她当董事长。她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那时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竟热乎一阵,想要办汽车公司。
她在《赵家杂记》中将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邻居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了请赵太太来帮帮忙。那个时候,金先生那时正跟一位LilianTaylor小姐谈朋友,杨以为出了什么要紧事,申明犯法的事绝对不做。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家的一只大母鸡营养太好生不出蛋,请杨医生帮忙助产蛋。
杨步伟是个人未到,声已闻的大嗓门,和清华园里的诸多学者十分相熟。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发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杨步伟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她那桌却笑语不绝。
1946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他们的证婚人胡适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以志祝贺:
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
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71年6月1日是两人金婚纪念日,赵元任夫妇步胡适《贺银婚》之韵又各写《金婚诗》一首。
杨步伟是这样写的:
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
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
赵元任的答词是:
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
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没有灿烂的鲜花,没有甜蜜的话语。就在这样平白如话的应和唱答间,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夫妻之情表跃然纸上。
赵元任和他的好友胡适一样,都有怕老婆的名声。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杨步伟也毫不讳言:“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
上世纪20年代,留洋回国的海龟们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仑跟赵元任开玩笑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赵元任哈哈大笑,“女大三,抱金砖”。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这部自传用英文出版之际,杨步伟请赵元任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提笔就写道:“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不愧是造诣高深的语言大师,赵元任的冷幽默令人捧腹。跟随他俩生活多年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有一次胡适问杨步伟,平时在家里谁说了算?她很谦虚地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她不忘了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得成比目何辞死,只羡鸳鸯不羡仙”。赵元任和杨步伟这样一对鹣鲽情深,相濡以沫的夫妻,被后人称为“神仙眷侣”。是赵元任的宽容成就了杨步伟的干练;是杨步伟的热情涵养了赵元任的沉静。他们用恬淡而深情的厮守,演绎了平凡而真挚的爱情。
“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在那个思想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杨步伟以特立独行的思想开辟出一条新路,成为新女性的楷模;在事业的巅峰时刻,她又急流勇退,扮演起了相夫教子的角色,日复一日地为柴米油盐操劳。即便放在人们思想空前解放的今天,我们也很难理解她甘愿隐身幕后,默默奉献的举动。但她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给了我们一个赏心悦目的答案。
她说“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地道的中国女人”。是的,她的确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但她却凭尽着自己的力量,把一个普通地道的中国女人做到了极致。
杨步伟与赵元任
尽管关注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已经很长时间了。直到今天,我还说不清楚,是杨步伟让赵元任走向普罗大众还是赵元任让杨步伟名声远播。或许,这只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悖论。他们相敬如宾,珠联璧合的情感生活,本身就是一段历久弥新的佳话。
杨步伟祖籍安徽石台,1889年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按照传统习惯,一岁时要“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后来,杨步伟对此解释道: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或许,苍天在冥冥之中已经无言地把人生的运程展示。这些,在她以后的人生中似乎都得到了应验。
幼年时的杨步伟天真烂漫,无拘无束。因她脚大,家里人喊她叫大脚;因她小时瘦而高,送给她“天灯杆子”的绰号;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干。家里人亲昵地骂她“搅人精”。
优裕的家境,是她从小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先生教她《论语》,当读到“割不正不食”时,她批评孔子浪费:“他只吃方方正正的肉,那谁吃他割下来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父母骂她不敬圣人;读《百家姓》,她取笑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王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一副童言无忌的样子。
1895年,杨步伟的生父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的施工管理。正在两江总督张之洞门下的黎元洪负责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杨步伟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黎元洪和她闹着玩,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说她放的雪人弄湿了他的被子。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还了五下,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黎元洪对杨步伟十分欢喜,杨步伟从日本学医归来后,得到了黎元洪十万元的捐助,她的医院才得以开张。
16岁那年,杨步伟参加南京旅宁学堂考试,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这样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在那个男权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不啻是一声惊雷!然而,和绝大多数女子一样,彼时的她并没有摆脱家庭的羁绊:刚出生前父母做主与表弟指腹为婚。就在这年,家里正式下了定婚礼,要她嫁给二表弟,她不干,坚决要退婚。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要死要活,家里被闹得鸡犬不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了,但要她声明终生不嫁。生父气得半死,要将她捉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开明的祖父出面,才收了场。她以不屈的抗争换回了自由,这场胜利,使她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1912年,时任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办了崇实学校,培养训练500多人的北伐女子敢死队员。22岁的杨步伟担纲当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结绒绳,刺绣,学救护,轰轰烈烈。还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赵元任与杨步伟的恋爱始于1920年。那是9月的一个晚上,赵元任从国语统一会散会出来,因时间太晚西直门城门已关,回不了清华,就去表哥庞敦敏家过夜。那天表哥家正好有客人,都是留学日本归来的朋友,其中两位是森仁产科医院的女医生杨步伟和李贯中,第二天两位女医生请庞敦敏夫妇到中央公园吃饭,作为庞家客人赵元任也应邀请做客。赵元任对两位女医生印象很深刻,称她们“这两位大夫是百分之百的开通”。
饭后大家到杨步伟的森仁医院,他们吃了法国点心,美国巧克力糖,赵元任唱美国歌,表哥表嫂唱昆曲。从此赵元任便成了森仁医院的常客,杨步伟在自传里说,她本想成全赵元任和李贯中的结合,自己尽量躲开,谁知最后成全的却是赵元任和杨步伟。
那时,英国哲学家罗素正在北京讲学,有一次同杨步伟出去游玩回来晚了,罗素只好坐在讲台上干等着,当他看见赵元任带着女朋友进礼堂时就全明白了,罗素指着他笑着轻轻说:"Badboy,badboy!"
赵元任后来记述了他与杨步伟如何确定终身大事的细节:“(1921年春)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韵卿(杨步伟)问明天早上能不能去看她,她说可以,她会在家的。我说我要在中山公园西山坡上见她。七点钟她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山顶上等了。‘你那么高啊!赵先生。'这是她说‘早哇'的另一种方法。我走下山坡对她说:‘杨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可是我怕你可能伤害她,而对她没有好处。我愿意一切美好,不过我不能老让她误会。也许像我以前说的,我应该少来看你们,可是为什么我该--'我说了半句停止不说了,和她在公园里静静地走来走去,最后在公理战胜碑前停下来,她说:‘对了,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于我也最好。'说了她就转身走开。‘韵卿(杨步伟的字)!(这一回才终于叫出了名字)'我亲切地叫她,她回过头来。‘韵卿,'我又叫一声,‘就那么算了吗?--我是说咱们?'我怕她会回答:‘咱们?怎么叫咱们?'但是她未作声,向我走过来。”
1921年6月1日,32岁的杨步伟和29岁的赵元任举办了一场独出心裁的婚礼。这一天上午,他们在北京市小雅宝胡同49号住处,请老朋友胡适还有杨步伟的同行朱徵小姐一块儿吃饭。
由杨步伟亲自下厨做四样美味的小菜。饭后,赵元任微笑着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朱徵大夫和胡适先生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回忆道:“我的同班同学胡适劝我们至少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才算合法。”
然后,赵元任杨步伟到中山公园,自照了多张相片,决定以在格言亭拍的一张,跟“结婚(或无仪式结婚)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写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
在发给亲戚和朋友们的结婚通知书上,他们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们末到之先已经在“十年六月一日(就是西历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通知书上定的结婚的那时刻,两个人正在邮局给亲友发给结婚通知书呢。
翌日,《北京晨报》以“新人物新式婚姻”为标准题,“新夫妇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证婚人胡适之与朱徵女士”“新式婚书”“新式的通知书”四个副标题报道了他们的结婚消息。报上说这个结婚式不但在中国,就在世界,也算得一种最简单最近理的结婚式。当赵元任问罗素这种没有仪式的结婚仪式是否太保守时,罗素回答“这够激进了!”
事后,这对不谙人情世故的书生还因为真的退掉礼物而得罪了亲戚。最喜爱赵元任的姑妈送来一个花篮,也被退回了——因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但此后赵元任一直在追悔,那个花篮总可看作精心制作的祝贺卡片呀!
对于他们不落俗套的婚礼,杨步伟一直引以为豪:“我们当时这无仪式的结婚仪式,不但是在那时轰动一时,就是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要说学赵元任夫妇的结婚仪式,但是没有一次学象了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女儿们也学不象。”
婚后,杨步伟舍弃了自己主持的医院院长和妇科主任职务,当做起了“全职太太”。但她是位“闲着就难受”的女性。
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太太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佯作不知,不闻不问,落得个清净。而杨步伟依旧我行我素,乐此不疲。遗憾的还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反而赔本关张,杨步伟投资的400银圆全砸进去啦。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退出了小饭馆,杨步伟又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还办了个“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以至遭到政府“窝匪罪”的指控,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杨步伟重情仗义,古道热肠。她的的同学林贯虹病死后,她张罗着将她的遗体送回老家福建安葬。她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帮助死者亲属。后来,清华大学为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创办了成志小学,请她当董事长。她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那时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竟热乎一阵,想要办汽车公司。
她在《赵家杂记》中将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邻居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了请赵太太来帮帮忙。那个时候,金先生那时正跟一位LilianTaylor小姐谈朋友,杨以为出了什么要紧事,申明犯法的事绝对不做。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家的一只大母鸡营养太好生不出蛋,请杨医生帮忙助产蛋。
杨步伟是个人未到,声已闻的大嗓门,和清华园里的诸多学者十分相熟。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发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杨步伟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她那桌却笑语不绝。
1946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他们的证婚人胡适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以志祝贺:
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
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71年6月1日是两人金婚纪念日,赵元任夫妇步胡适《贺银婚》之韵又各写《金婚诗》一首。
杨步伟是这样写的:
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
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
赵元任的答词是:
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
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没有灿烂的鲜花,没有甜蜜的话语。就在这样平白如话的应和唱答间,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夫妻之情表跃然纸上。
赵元任和他的好友胡适一样,都有怕老婆的名声。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杨步伟也毫不讳言:“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
上世纪20年代,留洋回国的海龟们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仑跟赵元任开玩笑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赵元任哈哈大笑,“女大三,抱金砖”。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这部自传用英文出版之际,杨步伟请赵元任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提笔就写道:“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不愧是造诣高深的语言大师,赵元任的冷幽默令人捧腹。跟随他俩生活多年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有一次胡适问杨步伟,平时在家里谁说了算?她很谦虚地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她不忘了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得成比目何辞死,只羡鸳鸯不羡仙”。赵元任和杨步伟这样一对鹣鲽情深,相濡以沫的夫妻,被后人称为“神仙眷侣”。是赵元任的宽容成就了杨步伟的干练;是杨步伟的热情涵养了赵元任的沉静。他们用恬淡而深情的厮守,演绎了平凡而真挚的爱情。
“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在那个思想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杨步伟以特立独行的思想开辟出一条新路,成为新女性的楷模;在事业的巅峰时刻,她又急流勇退,扮演起了相夫教子的角色,日复一日地为柴米油盐操劳。即便放在人们思想空前解放的今天,我们也很难理解她甘愿隐身幕后,默默奉献的举动。但她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给了我们一个赏心悦目的答案。
她说“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地道的中国女人”。是的,她的确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但她却凭尽着自己的力量,把一个普通地道的中国女人做到了极致。
杨步伟相关资讯
-
杨步伟:民国最早新女性
2011-10-14 / 12958 Views / 0 Comments杨步伟人如其名,慷慨干练洒脱。她胆大,刚去日本留学的时候,自己尚不精日语,便带着两个人从长崎去东京,路上坐错车,走错路,不过最后竟也到了东京。与丈夫刚到美国便发现怀孕,说起来此时丈夫应当努力养家才是,但赵元任此人一向可不弄钱便不弄钱,到了哈佛只接了一项批